钱塘传奇(我与一座城)
 |
|
图为钱塘江大潮景色。 |
如果有人跟我说起钱塘江,我马上就想对他讲讲钱塘潮。钱塘潮是钱塘江与生俱来的胎记,钱塘江是钱塘区的“形象代言人”。
我的老家在飞云江畔。小时候,每当涨潮时,我就来到楼顶看江水。在村子的渡口码头前,从分岔口涌进来的江水犹如千百只鸭子在赶路,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潮水跑到我家院子后面,就没力气了,慢慢不见了。“这个潮水没什么好看的。”父亲说:“你要看就去杭州,钱塘潮水天下第一。”
二十多年后,我来钱塘区当老师,住在了钱塘江边。农历八月十八,钱塘江面潮水如万千白马飞驰而来,声如雷,鬃如雪。那一刻,冲上来的潮水恍若要将沧海淘空。原来,宋代潘阆“来疑沧海尽成空”不是虚言。
我发现钱塘江的壮美和钱塘人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。钱塘人印一本小册子,选奔涌的潮水当封面;过节摆个花圃,也要配成浪花的模样;出品的各种宣传片,钱塘江总是不可或缺的“第一主演”……钱塘区要做徽标,老百姓从全球征集的500多份设计方案中,挑中了蓝色的逐浪款和金色的旭日款。两者都是以钱塘江作为主要元素,难以取舍,遂两个都要了。于是乎电梯口、地铁上、学校里,随处可见两个波涛翻涌的徽标。
我还发觉钱塘人有事没事喜欢往江边跑。钱塘江又叫之江,因其江道曲折,形状如汉字“之”。区内道路都是井字形,所以不管横路还是竖路,最终每一条路都通向了钱塘江,车开着开着就驶到江边了,人走着走着就逛到堤上了。有潮的时候看潮,没潮的时候看桥,看树林,看芦苇荡。我喜欢在江边跑步吹风,看高树枝头叶子乱颤,大树下、帐篷边的小孩在嬉闹。几十公里长的堤坝上有人拍视频,跑步,骑车,钓鱼,放风筝,扛着个音响开独唱会。
刚来钱塘时,我很好奇,钱塘人为什么如此迷恋看潮、看江、看堤?后来,我细细研读了钱塘区的历史资料,终于找到了答案。
钱塘区怀抱着钱塘江,钱塘江哺育和滋养了这一片土地。我看到赞扬钱塘江大潮的文章何其多,但壮观之下的民生之艰,让人扼腕。钱塘江自古常发生坍江事故。木柴塘,泥土堤,遇上大风大潮,两岸的家园就会被吞噬。南岸塌了,渡江到北岸过日子,北岸塌了,又渡江回南岸讨生活。钱塘人自嘲是“沙头鸟”,在江南、江北飞来飞去,不知何处可落脚。
新中国成立后,为治理水患,钱塘人开展了几次大规模围垦活动。钱塘江潮水凶猛,“虎口”夺地,难度可想而知,只能选择潮水比较小的冬季进行。从当年的影像资料中,我看到这样的情景:在天寒地冻的日子,几万名军人和钱塘人赤脚在湿滑的滩涂上和时间赛跑。江水里的薄冰像刀,割进皮肤,脚上腿上时常会豁出血口子。
在围垦文化节的现场,我听多位耄耋老人讲述当年故事,他们“喝咸水,住草舍,睡白沙滩,吃夹着小石子的米饭”。钱塘江边水汽重,睡在白沙滩,像是半个身子泡在江水里。十几岁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,只是一心想着把堤坝筑起来,把潮水挡出去,把家守护住。常年江水冲刷,围垦出来的土地大多数是盐碱地、流沙土。盐碱地能种什么?只能种点萝卜。至于流沙土,更是可怕。但对于在潮水中抢潮头鱼、筑堤坝、讨生活的钱塘人而言,总有办法让这片贫瘠的土地长出庄稼。
最终,钱塘人从钱塘江的怀里接手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,通过科学治理和技术创新,将碱地化为沃土。
我站在钱塘江绿堤上,看向江的南面,对面有麦浪、稻田和花海,江的北面有汇聚十四所高校的大学城、高科技产业集聚的科学城。宜居,宜学,宜业。从滩涂上走出来的钱塘,变成了一座夜空灯光特别闪耀的城市,再续“钱塘自古繁华”新篇章。
每一次父母来钱塘,他们也像在老家一样喜欢到江边散步漫游。春天,他们看不知尽头在何处的晚樱。如果恰好在农历八月,他们就去看潮水。我告诉父亲钱塘的沃土是怎么得来后,他很震惊。父亲是一个农民,他深知土地的宝贵与来之不易。父亲对此念念不忘,回老家后,他跟很多朋友讲起钱塘江潮水,讲钱塘人六十年来奔竞不息的故事。
在钱塘的十年时间,我看钱塘潮涌,听钱塘故事,写钱塘传奇,我时刻感受到钱塘人血脉中的弄潮儿精神。江边潮起,风混着水汽与青草香,于我是那么的亲切。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1年12月27日 20 版)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推荐阅读
相关新闻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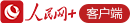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